打了电话,那边是个沉稳的声音,问了问情况,约了个时间。等着师傅来的过程,简直煎熬。盯着那不转的扇叶,听着它发出那种“呜呜”的无力声,只想快点,再快点。
终于,门铃响了。开门一看,果然,一位老师傅,个子不高,但看着挺结实,手里拎着一个工具包,肩膀上还背着另一个,沉甸甸的。脸上晒得黝黑,眼角有些细纹,估计是常年迎着太阳高空作业留下的印记。没多余的寒暄,一句“您好,空调坏了是吧?”,就开始往里走,直接走向那个“病人”——我的内机。

他站那儿,先不急着动手,而是听。耳朵凑近出风口,听那声音,又摸摸外壳。就像老中医望闻问切似的。然后拿出遥控器,开开、关关,试了几个模式。眉头微微皱着,眼神却很专注。那种不慌不忙,自带一股子定海神针的气场。这,就是经验。多少书本知识,也换不来这双耳朵、这双手的感知力。
“压缩机好像启动了,但压力不对,”他低声自语,然后抬头看了看我的外机位置,“得去外面看看。”得,最麻烦的一步来了。我家住三楼,外机挂在窗户外面,想够着它,非得探出身去不可。对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来说,光想想就腿软。
师傅却好像习以为常,从工具包里拿出安全绳、保险扣,熟练地固定在窗户边上。看他动作麻利,但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,你知道这高空作业,可不是闹着玩儿的,稍有不慎,就是拿命开玩笑。我站在一边儿,大气都不敢出。
他小心翼翼地跨出窗外,半个身子悬在半空中,头顶是毒辣的太阳,脚下是晃眼的地面。汗水瞬间就从他额头、脸颊淌下来,把衣领都浸湿了。他用随身带着的小扳手、螺丝刀,打开了外机的外壳,露出里面盘根错节的管线和风扇。那些复杂的电路板、铜管,在我看来就像外星文,他却一眼就能找到目标。
捣鼓了一阵儿,又是测压力,又是量温度。他嘴里时不时冒出一些我听不懂的专业词汇,“制冷剂不够了”、“毛细管好像堵了”、“风扇电机有点虚”…听着这些,我心里直打鼓,这得花多少钱啊?
最后,他确定了问题所在。原来是制冷剂跑光了,加上外机风扇电机有点老化,效率不高。得加氟,还得看看电机能不能抢救一下,不行就得换零件。
加氟的过程,看着简单,其实是个技术活儿。他接上管子,看着压力表,一点一点地往里加。眼神还是那么专注,生怕多一点或少一点。他说,这玩意儿加多了不行,少了也不行,得刚刚好。这手艺,全靠日积月累。
电机呢,他拆下来,清理了清理,加了点润滑油,又仔细检查了线圈。他说,这电机还能凑合用,但下次可能还得换新的。听他这么说,心里暖暖的,没有那种“坏一点点就让全换”的套路。
终于,一切搞定。他小心地装好外机外壳,解开安全绳,从窗外跨了进来。脸上、胳膊上全是油污和灰尘,衣服湿得能拧出水来。但他的眼神告诉我,活儿干完了,没问题了。
回到屋里,他让我开机试试。按下遥控器,内机重新启动。这一次,声音明显不一样了,带着一种有力的嗡嗡声。然后,一股沁人心脾的凉风,缓缓地、但坚定地吹了出来。那一刻,那种被拯救的感觉,简直无与伦比!整个房间的闷热感,在凉风的驱赶下,一点点消散。
师傅坐在地上,稍微休息了一下,喝了口我递过去的凉水。我看他,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。不是坐在空调房里敲键盘、滑鼠标的,而是顶着烈日、冒着风险,靠一双脏兮兮的手,靠脑子里的知识和长年累月的经验,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人。他们用自己的汗水,换来了我们的清凉舒适。
聊了几句,他说这行现在不好干了,年轻人愿意学的少,又脏又累又危险,挣的也是辛苦钱。但没办法,总得有人干不是?城市这么大,哪家哪户离得了空调?离得了他们这些跑腿的师傅?
看着他收拾工具,那些扳手、螺丝刀、压力表,在他手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样,服服帖帖地各归其位。那工具包,仿佛是他的移动战场,里面装着解决各种故障的武器。
他临走时,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,比如多久清洗一次过滤网啊,外机周围不要堆杂物啊等等。朴实的话语里,透着一股子负责任劲儿。
关上门,屋里已经完全凉快下来。站在窗前,看着楼下外机的风扇欢快地转着,心里涌上一阵感激。这不仅仅是修好了一台机器,更是修好了这个家在炎热夏日里的“命门”。一个空调师傅的维修,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劳作,是面对危险时的淡然,是那份靠手艺吃饭的硬气。下次再听到空调发出奇怪的噪音,再遇到故障,我知道该找谁。他们就是这座城市里,默默无闻的“清凉守护者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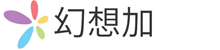

评论